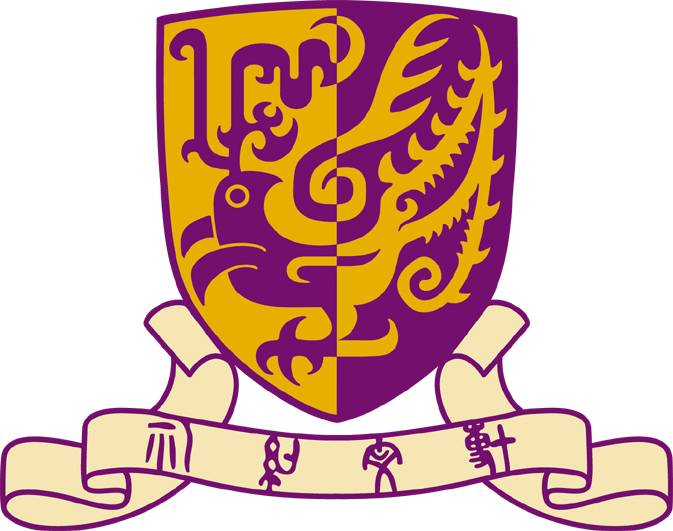「我從小到大都喜歡文學,大學開始玩樂器和嘗試填詞。但我覺得這和專門去讀這些科目,是兩件事來的。創作的世界很大,多接觸不同的社群與文化,可能更能刺激你的思考。」陳心遙(Saville)在大學修讀人類學,畢業之後,對電影的興趣愈發濃厚,慢慢開始在這個行業尋找機會。「讀書的時候就喜歡看電影,之後越看越多,就嘗試接一些短片、廣告的project來邊做邊學,由不懂學到懂。」
但當被問到有何入行經驗可作分享時,Saville卻是「拒絕」的。「世界變得太快,如果我答了、別人真的信了,會害人的!」在Saville看來,隨著社會的變遷、科技的進步,即使一個普通年輕人,影片製作技術可能亦已經非常純熟。「我認識一些編劇、導演,說到拍片、剪片,他們的仔女比他們更加叻!這是一個視像爆炸的年代,人人拿著電話、人人有部電腦,人人都有不同的方法,可以製作出好看的影像。」前輩的經驗,到了今時今日未必適用,很難以一條定律來說年輕人應該怎樣做。但話說回來,「製作技術可能很多人都會,但那不是作品的全部。『創作』不是只靠技術去實現的,而是要對世界有多些認識、再從你自己的獨特角度去理解、詮釋。」
說到創作,靈感與養分從何而來?Saville的作品,如《狂舞派》、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,常被形容為「本土電影」。 「但我沒有刻意去想本不本土這些問題……創作本來就是源自生活的喇!我在哪裡生活,就最容易寫得到哪裡的故事,這是很自然的。」但這並不是說,創作者要固步自封、固守己見;Saville解釋,在近年的合拍片熱潮之中,不少著名的香港導演要到中國大陸拍攝電影,也會先在當地居住生活一段時間。「要寫出貼地的劇本、拍出觸動人心的故事,始終是要瞭解民情、紮根於一個地方的。所以我覺得,『本土』這個概念,要有多點思考和討論才有意思,不然就容易變成純粹是情緒宣洩、標籤噱頭了。」不過,Saville又補充,「電影的生命有很多人參與:電影拍出來,誰幫你剪預告片、誰寫廣告語、誰安排宣傳活動、誰協調院線排片……都是團隊工作來的,其中有很多經濟的考量。我自己或許不會刻意要宣傳『本土』,但發行公司也可能有他們的判斷。那我會覺得,在一個自由的市場之中,這是沒有問題的;觀眾不是傻的嘛!宣傳是和觀眾的一個博弈,如果只是賣本土情懷但電影不好看,試多兩次,觀眾就不會買賬了。最緊要是有一個自由的、大家可以選擇的創作氣氛;最重要的始終是作品本身。」
身兼編劇、監製、作詞人等多種角色,Saville怎樣看香港電影與音樂的發展前景呢?「我沒有特別悲觀,也不是特別樂觀;事情始終是要做、有些東西始終是不會消失的。就說電台吧,我讀書的時候都已經說是夕陽行業,但我畢業後在電台工作了很多年,直到現在我離開電台了,廣播電台也還未消失喔!電影也一樣,可能未必有最風光的時候那麼高收入、那麼多人注意,但它是會繼續存在的。電影也只是一個format, 可能以後最流行的變成廣告、網劇、短片,但總而言之,觀眾不會突然對『用影像去說故事』這件事完全失去興趣的。放在一個大世界裡看,我所做的創作,所需要的資源其實很少;那就去和其他人競爭囉,競爭是現實來的,不能迴避。出路不是想出來,是做出來的嘛。」
同樣,大學的數年時光,放到整個人生裡看,也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。「有些師弟師妹,讀書的時候會擔憂將來的發展,這很正常。但我覺得也不用過分逼迫自己,甚至反而浪費了這幾年自由自在、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的階段——到你出來工作就會發現,可以選擇的空間越來越小,因為你的時間都被別人買走了。」Saville說,回過頭,他也會想,自己讀大學的時候,是不是應該不要那麼懶呢?不只是說讀書、學習,也是說,不要那麼懶不去玩——自己鍾意、有興趣、好玩的東西,就應該趁有時間多點去做。
更何況,人類學這學科本身的優勢,就是要讓同學去打開眼睛看世界。談到人類學訓練對他的影響,Saville以編劇工作為例:「人物是劇本的核心,人物寫得好,很多問題都會解決。但對於你要寫的某一類人,你本身可能是沒什麼認識的,那怎麼辦呢?不外乎是靠想像、靠在其他作品中得出的觀感、甚至是刻板印象。我想,最好的方法,是在當下找一些真的是這樣的人,和他們傾談,而這exactly就是人類學家在做田野考察時做的事啊。又譬如,在戲劇裡面,不同角色之間是各有關聯的。你寫一個『反派』,是想令觀眾更加瞭解那個『正派』的主角是一個怎樣的人。而在人類學裡面,去探索異文化,最終也是想瞭解自己:世界連成一線,『他者』總是相對於『自我』而言的。這種概念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啊!」在創作過程中,一些看似沒有用的東西,可能其實最有用。Saville笑言,「我是我,我是這樣去思考、創作,一些人類學的思維,已經潛移默化地在其中啦。」